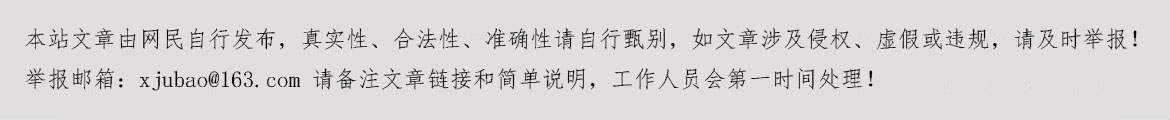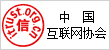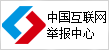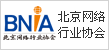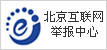布兰奇信息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,汇集美食文化、投资理财、国际资讯、热点新闻、商旅生涯、生活百科、等多方面权威信息
任长志:路上
2021-11-16 20:37:00
研究这个世界, 解释它或者鄙弃它, 对于大思想家或许很重要; 但我以为唯一重要的就是去爱这个世界, 而不是去鄙弃它。
——赫尔曼·黑塞
(零)
思绪飘回初冬的清晨,那里静悄悄。
万物抛去躁动,归于沉静的1/4。天际是完整的一片紫,有阵风吹来,昨夜的最后一片云也不见了踪影。深红的树立着,昏黄的路灯立着,城市睡着,只有我带起风,揣着跃跃欲试,逃也似地飞走。
风停息了,曦打破那层雾霭,打散最后一丝别离的酸涩。别想我,我的心舒坦着。我带着我的笔,就要向西远行。
(一)
入川。走一路,且看一路。
河南的边界上,田地是矩形的一片一片,金黄色,闪耀着。柯老师说这是还没有收获的小麦,我看了又看,最终什么也没有看出来。其实,我的爷爷就是农民,我的奶奶现在还在湖南老家孜孜不倦地耕作着,我身体里流淌着中国农民温热的血液,我的双螺旋结构中埋藏着对农耕的感知。但当我出生,长大,学习知识,我却对小麦的形状毫无概念了。瞬间有种怅然若失。
到秦豫交界,过隧道便成了常态。
这是一种太奇妙的感觉。北方特有的布满黄土的天就笼罩在前方,一层层巨大的山肆无忌惮地生长着,给人以无法言喻的震惊,甚至令我产生某种恐惧。但火车毅然决然地闯了过去,没有留给我犹豫的时间,就穿过了隧道。 心里有释然也有怀疑:我们就这样征服了大山?山回答了,以车与轨道摩擦产生的巨大轰鸣。我想这是它的不甘与服输。
在郑州,看见十字路口一角上,挺立着一丛层层叠叠的树。有深红,有浓郁的黄,居然还有深绿;在陕西,路过一个叫做佛坪的小县。一路上都在过长长的隧道, 突然闪过一丝光亮。这光亮中有一座座交叠的山静止着,被秋天染成了不均匀的深黄橙红,烂漫至极,仿佛浓郁地要滴下来。一团团渺远的雾缓慢地流淌着,环抱住山巅,散不开也不想散开。我向来相信大自然的审美,却也很难想象十一月凋敝了的天,是怎样造就了这么夺目的色彩。我说不清,道不明,便只是静静地目送它们向后飞驰。树那色彩、山与雾也都只是无言地交织在一起,在我心里静止下来,美极。
(二)
见人。
在青城山,身旁环绕的是仿佛虚幻的葱郁,看的却是真切的生活。
脚夫背着装满货物的,竹编的箩筐,拄着磨得发亮的拐,一步一步向深处走。他脸色灰黄,布满皱纹,眼睛似乎有些疾病,堪堪能睁开。他穿一身发白的迷彩服, 裤脚挽起来,露出静脉曲张的、的小腿。我久久地望向他,他低头,久久地望向大地。没有多余的神情,一下一下地抬着脚。
卖雪莲的婆婆静静站着。她一身花布衣裳,头发全白了,颜色调起来,像李自健的一张画。我走过她,她粗糙的双手扯上衣服,似乎想说点什么,却拘谨着,最终也没有叫卖。
我停下脚,走回她面前。她脸上闪过一丝欣喜,抄起那把黑色刮刀,给我削雪莲。我沉默一会儿,问,“阿婆今年多大了?”她怔了怔,随即垂下头,眼睛微微闭了闭,“马上该满七十啦。”我本还能再多说些什么,却什么都没说。雪莲被她飞速刨得光洁,我接过道谢,转身要离开。最后一眼望向她时,她像之前一样,静静站着,望山上的路,等着谁。
我永远凝视他们。
我看不到所谓“渺小的生命征服大山”,更看不到有人评价“这就是生活,生活就这样。不要太共情,不要太偏执。”这不是怜悯做祟,不是同情后转头过自己的人生,这是永远的深思。
乔治·奥威尔在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》里写:“所有的体力劳动都是这样,我们依赖他人的劳动而生存,而我们对这一切熟视无睹。矿工们有资格作为劳工界的代表,不仅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,而且因为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必要,却又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,如此不为人知,我们总是忘记他们的存在,就像我们忘记了身上血液的存在一样。看着矿工们工作,我们会感到羞耻,因为你会怀疑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上等人的身份。当你看着矿工们时,你会意识到,正是他们挥汗如雨的劳动才使得上等人能过上优裕的生活。”
他是对的。承受生活重压的人们,日复一日地背着箩筐,沉默,那是生活无情赋予的;我躲在繁华的城市,完满的家庭里,过着安逸稳定的生活,有时我也为了生命里的不如意哭泣,假装讨厌自己的生活,但我清楚我前路清晰。
有时我觉得愧对。那些蜡黄褶皱的面庞、粗糙的指尖、蜷缩的背,让我感到无力。我只是窥见了其中的一隅,我该做什么?
仔细想,只有去理解。记住那些苦难,记住那些面庞,记住拄杖行走,记住静立的背影,然后写下来。
在大足石刻。
有僧侣。他穿一身棕红的袈裟,一晃一晃,在喧嚣的人群里游。他眼微闭,眉平直着,也不恼。他一手放胸前,握住包袱,一手放侧,轻轻贴着,时不时低头,向身旁的讲解轻声问些什么,大抵是关于石刻的。讲解指给他看,他便又抬起头,望向那漆黑一片的洞窟,可我分明看见他眼里的光。
有写生者。她静坐在沿阶的围栏旁,穿一身翠绿的大袖长袍,抱着块墨绿的写生板,握着只竹色的笔,和这烂漫的山色融化在一起。她频繁地抬头望向石刻,望向山林,又频繁地低头,一点点描摹轮廓。她神情淡淡的,微翘的嘴角却出卖了她的欣喜。或许是为了苍翠的林,为了有微润光辉的石刻,我不知道,但这一幕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很久。队伍在向前走,我最后再看了一眼。看见她四周的尘埃忽被透过树叶的光照亮,轻舞着,只是一霎。我怔住。她还是在那里,朦朦发着光,像人群中一个神明。
有游客。他一个人来,背着手,小步走在山上。他穿得并不妥帖,甚至连洁净都称不上。脸上灰黑着,眼和嘴紧绷着,非常沉默。可他那一对狭长的眼,紧紧盯着山间的石刻,时不时转动,折出碎了的光。我们走得很快,听完了,便要离开了。可我相信他花了很长的时间,用虔诚的目光抚摸石刻的每一个棱角,用心无限贴近。
这些虔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?我不好说。但这些人确实让我想起了二郎庙里反复敬香的人,想起挑吉日参拜佛寺的外婆,想起乡土的中国。当我们谈论神,谈论宗教,谈论信仰,总不自觉地将它们与平凡的生活割裂开,把它们变成华丽的,神圣的,疏远的东西。但在这些人眼里,神是一眼凝视,一抹化不开的墨色,一束照在石刻上久久不肯离去的光,仅此而已。
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。
在汶川。
缓缓行在乡间车道上,静静地想。温热的光洒过枝叶的缝隙,忽明忽暗。普通的冬日一天里,我沉默地踏入汶川大地震震源地——映秀镇,用我一颗早已摇晃不已的心,无限贴近2008年,5月21日,14时28分04秒摇晃不已的那一刻。
下车,忽然发现对于祭奠故去的灵魂来讲,这确实是个萧索的时节。没有清明时初醒的山川,没有中元时湿润的青绿苍翠。我站立着,只听见深秋无情的风拍打着摇摇欲坠的枯叶,发出孤独的“唦唦”声。远处有不知名的禽类独飞着,围绕着只见青影的山,长久地啼鸣,一圈又一圈。
站在漩口中学遗址外,接过苍白的菊花,一瓣一瓣地去掉花柄上的杂叶,心情似乎也苍白了起来。虽不止一次地想过现场的样貌,但当我瞥见时钟雕像后支离破碎的教学楼时,还是不禁湿了眼眶。
我一步、一步,缓缓地走进遗址,游荡在空中,落不下地。破败不堪的女生宿舍从中间撕裂开来,墙壁展示着无数斑驳丑陋的痕迹;教学楼或失去了一层,或一层一层重叠起来,倾斜着,玻璃碎了一窗,摇摇欲坠,发出了灭顶之灾下巨大的轰鸣。它在求救。我看着,想着,若这些庞然大物都没能抵抗撕裂的土地,那这里掩盖着的迷失的灵魂呢?他们有没有无助地呼喊,一遍又一遍?我的心随着犹如泣血的悠长号角,颤了又颤。我静默地站立,望着前方14点28分石碑,听着学姐一字一句的仪式宣告,心里全是血泪。
我听到很多故事。教师逃出教学楼后,一次又一次地逆人流而行,只为把孩子们全部送出;学生们被掩埋在废墟下,哭泣之时,有一个瘦小的姑娘愿意擦干眼泪,带所有同学唱歌;小男孩被救出时,没有急着吃饭喝水,他缓缓地、坚定地向消防官兵敬了一个军礼。当听到老师们郑重地讲述时,我的眼泪才终于沉沉地砸下,落入这片残破却竭力拥抱希望的土地。行前文集里收录了一篇文章,一位地震志愿者讲述自然无情的分崩离析使文明与秩序崩塌。但我在泪水模糊时,分明看见人性之花悄然绽放。
我看到漫布生机。在市井穿行中,人流带动一股蒸腾的世俗气息来来往往,好像那座悲伤的城隐去了形状;在漩口中学崩塌的屋顶上,我看漫布的苍翠绿草,是草木以摇摆的身躯覆盖伤痕。低下头看到遍布悲难的创伤痕迹,抬起头遥望无边的山,忽然觉得这是生命的交错生长。
我看见永远铭记。男孩与父亲默默地走在漩口中学破碎的建筑旁,男孩本是不懂事的年纪,但父亲牵着他的手,用质朴而乡土气的口音,一遍又一遍讲着这里的故事。父亲最后拉着他站定,在石碑前,好像是对儿子的告导,又好像只是在喃喃自语,“永远不要忘记。”我望着他们,一大一小缓缓地越走越远。小男孩忽然回过头,仿佛是感觉到我的目光。我们最后送给对方相视一笑。
回程路上,看到一段文字:“还是留下了汶川的色彩,毕竟,飞机撒下种子,今天已是多少人努力的青山又绿,我们还有千年间的不朽能让我们选择相信。”我长久地静默着,为它悲泣,也为它向往黎明。
在杜甫草堂。
走在细雨飘摇中。天被刷上一层厚重的灰,云有气无力地挂着,散作一团。草堂墨色的匾和深绿的叶上挂了许多露珠,闪着光,好想要诉说些什么。 行前读了太多关于杜甫的文章,此时却放空了,一脚踏上杜甫草堂潮湿的土地,任它以身躯诉说。
在裘马轻狂,意气飞扬的日子里,杜甫的生命中充斥着许多热切的愿望。他急切渴望着参与朝政,用一腔热血实现自己对国家的愿景。人们笑叹他生正逢时,这是属于所有人的大唐盛世。
父亲去世,家道中落,娶妻生子,担负起一家的责任。他开始为生活讨好折腰, 渐渐尝遍人间所有心酸苦楚。有人说这是独属他的生命痛苦,是他无法逃脱的牢笼。但当国破家亡,大唐的壮美山河染上洗不去的血色时,他满眼只剩下数不清的尸骨与散不掉的忧愤愁思。他的心中不再仅存得下个人的命运,而是与战争——这大唐的命运作斗争。
他看到了被强征的壮丁,再等不回子女的垂老妇人,于是用笔书写他看见的,想的,做的,分担本不属于她的痛苦和无助。他的生命境界在无限伸长:从记录一个人的不幸——在一个貌似国泰民安、四海升平的时代中,一个充满才情与志向的诗人四处碰壁,在他人得意之时恒久地,辛酸地生活着;到记录一个家庭的不幸——贫穷、饥饿、温饱难全的现实时刻都在杀死他们生的希望,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; 最终记录一个时代的不幸——腐化的朝政,贪图享乐的皇帝官员,一个个被役使、被压迫、被剥夺生命的黎民书写了这幅悲剧的,空洞的时代画卷。
他懂命运的残酷,但他垂垂老矣之时,仍以残破的身躯大声向命运质问。最终成就了他的伟大与不朽。
说命运二字的时,两声仄有力地响,宛若刀削,毫不留情。它见惯无力的众生, 悉知如何残酷。但杜甫站在这里,以所有听过见过的与命运殊死一搏。他不要求命运给什么公道,只是发誓不哭,不低头,不轻易接受苦难。他看世界上所有光芒万丈, 也懂最坏的还没有来,黑暗终会降临,但还是永远高昂着头,反反复复,永不停歇地质问命运,一任头破血流。
怎么能不把他的故事读了再读。
(三)
见万般景象。
在武侯祠。
成都午后的阳光是躁动的。它放肆地洒在我脸上,绽出一朵朵模糊,烫得左摆右摆,急着用手遮挡。
可在这躁动的时间,武侯祠却安静的伫立在那里,以它青绿深沉的姿态。一只脚踏进武侯祠,铺天盖地的,浓郁的绿便包裹住了一切。青灰色的石雕吐露着冰冷的气息,它在诉说这里风雨流转。几十代人来来往往,暗绿或青翠的植株却只是高耸着, 层层叠叠,散发清冷而和煦的气息。武侯祠显示出它湿润的、安静的内里,像一个老者伸出手,深沉而有力量。
抬头看那些蜀汉良臣的塑像。这些塑像并不精美,饱和度极高的色彩堆叠在一起,配以几张一模一样的人脸,甚至有些滑稽。但我轻轻走过它们,以绝对的静默。抬头看书写他们一生功绩的匾额,低头看清人为他们细细篆刻的生平,一群形色各异的人,为了一个国家的存亡聚集在四川一片小小的平原上,或在朝堂奉献一生心血,或在沙场上为国争先,这种个体的奉献合起来,便成为了一种伟大。
难怪,长长的游学队伍里混进许多成年人,他们倾听极其专注,时不时发出一声悠长的感叹;难怪,惠陵前,诸葛祠堂后,放着几株祭祀用的,清秀淡雅的花,默默地开放,为祠堂添了几分清香;难怪,人文学子静立在小后门前,把《蜀相》《出师表》一读再读......这是武侯祠赐予的,我们的郑重。
在蜀南竹海。
走在竹海里。不经意时有露珠滴落,染上了秋雨的湿润,像被无言的竹海亲吻。雨后深浅不一的,铺天盖地的绿意完全包裹住我,扑面而来,仿佛也是一场雨。这是一个完全纯洁的环境,只有竹和路。那么便攀着竹,踏着石阶,以最无趣的姿态,一直不停地向上走吧,最终竟也到了终点。
有时候我也想,年轻的我们被赋予了太多。有没有目标,敢不敢挑战,每时每刻都在思考自己走这一遭到底要去向哪里。我彷徨的迷茫的,竹海全都懂,它只是在细雨中低语,教给我别犹豫,别停,走。
所以在一个下午把自己完全交给竹海,与它进行最原始的互相问候。抛弃那些念想,抛弃患得患失,抛弃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一切。随竹海中万物沉淀。
(四)
梦里忽明忽暗时,总有猩红色的天幕从地平线展开,灰黑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。我在穹顶下走着,飞快地走着,不知道路在哪里,也不知道我走在哪里。忽然惊醒才发觉,夜已经很深了。
于是逃跑了,跑向一个足以放空的地方。到如今,最笃定的还是“用笔书写我的行走”。这是我的坚持,于是择日兑现。